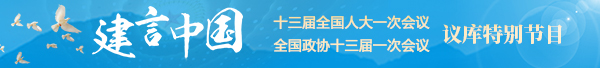艾克拜尔?米吉提:中国作家的骄傲
在许多人眼里,作家只不过是写写文章罢了。其实,不然。于艾克拜尔·米吉提(以下简称“艾克拜尔”)来说,他不仅仅是著名作家,还是翻译家、评论家,上知天文,下知地理,知识渊博。
提起艾克拜尔·米吉提的名字,于文坛尽人皆知。在我所读的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二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时,由于实施抓阄确定导师,他便成了我们这届几位师兄师姐的导师。关艾克拜尔的故事,非常值得学习。
那年,他从不懂汉语开始
艾克拜尔是哈萨克族,是我国55个少数民族之一。哈萨克族有着自己的母语,在当地,他们用母语交流,而对于汉语,用他的话说,那就是一个“旱鸭子”。我们不难想象,他当初接触汉语,是花了多少苦功的。
他的父母都是医生。父亲对哈萨克语、俄语、维吾尔语、柯尔克孜语、乌兹别克语、塔塔尔语等样样精通,又是医科毕业,对拉丁文也有研究。当时,在父亲看来,汉语不仅笔画多而复杂,读音也奇异,所以,也只能说上几句罢了。母亲则不同了,在她17岁时,作为新疆牧区代表团成员,到内地参观了一年多时间,期间学会了汉语,还有幸受到毛主席、朱德、刘少奇、周总理等老一辈领袖们的亲切接见。
艾克拜尔慢慢长大了,用父亲的话说,要带他学一种大语言,那就是父亲认为的俄语。而由于他们不是前苏联侨民,而是中国公民,故没有所谓的苏侨证,于是,俄语学校就不招收他了。至此,父母带他到第十五小学,也就是当年伊宁市仅有的几所汉语学校之一,况且学校就在他们家所住的卫生学校后面。
到汉语学校学习,校方有所规定,首先孩子要懂汉语。当时,他对汉语一窍不通,待父母请求校方对其进行口试时,除了认得墙上挂的毛主席像,哪怕从“一”数到“十”,也是茫然。无奈之下,家长表示回去就教孩子汉语,第二天过来接受考试。最后,终得校方点头。艾克拜尔对汉语的学习,也正从这一天开始了。那是1961年的9月初。
掌握一门语言,从听不懂到熟练交流,一般而言,没有个一年半载,是很难的。所以,最初的三个月里,他除了用眼神交流,几乎什么也听不懂,就这样在班里度过了三个月的“哑巴期”。他置身一种语境之中,之后的日子里,用心听,用心记,用心学,最终搞清楚了自己所在的班级(一年级乙班),更令人欣喜的是,也可以开口与同学们交流了。自此,他认识到,汉语真的是博大精深,而且非常有韵味。
直到有一日,一位班主任去家访,通知他的父母,说六年级一毕业,就会将艾克拜尔送到北京中央民族学院附中上学,让家里人有所准备,勉励他要好好学习,不要辜负学校和组织的期望,同时,要求暂且保密,不透露出去此消息。
艾克拜尔还记得小学语文课《北京的秋天》,那时,他对北京秋日的蓝天、飞翔的鸽群、悦耳的鸽哨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,且充满了无限遐思,再加上从母亲的叙述里,也了解了北京。自此,北京成了他心中的一个梦想。遗憾的是,时代的动荡,让他的梦暂时破灭了。
于1969年8月,某日他到十五小学校园去转时,从八中招生海报上看到自己的名字。之后,便由小学六年级直升初三。在艾克拜尔的记忆里,随着珍宝岛事件和铁列克奇事件的发生,为了落实“深挖洞,广积粮,不称霸”的“最高指示”,学校开始组织挖防空洞,正常的教学秩序再次被打乱。
知青时期,全国要实行下乡。在他16岁那年,来到了伊宁县红星公社绿洲大队第三生产队,开始了下乡生活。干各种农活,包括种、收小麦,当过木匠,放过羊,学过兽医、当过翻译。农活干了大半年,他被调到“一打三反”落实政策“兵宣队”作翻译,也就在此时,恰遇公社书记到大队检查春耕生产,由于没带翻译,艾克拜尔被“赶鸭子上架”,临时做了公社书记的同期声翻译,巧的是书记懂维语,只不过是口语表达受限而已,他很欣赏艾克拜尔这个小伙子。不久,就指派艾克拜尔参加县委宣传部举办的通讯员的学习班,在学习班为期一个月的学习结束后,便被安排为公社党委通迅干事。
他从新闻写作开始,且研究《人民日报》《解放日报》《新疆日报》《伊犁日报》的头版,琢磨提法和报道特色,由此开始了新闻报道工作。其实,艾克拜尔小时候,受了父母和语文老师的影响,非常喜欢阅读,几乎每周都读一个长篇,尽管之前不太喜欢写作,自此时起,便与写作结了缘。也可以说,曾经的阅读给他的写作带来了益处。
1973年4月,包括王蒙先生在内的“三结合”创作组来到艾克拜尔所在的公社,创作连环画《血泪树》,由王蒙执笔写脚本。艾克拜尔负责接待他们并为他们作翻译。其他人都需要翻译,王蒙则不需要翻译。对此,他感到有些意外。经打听,得知此人是一位作家,听说还被毛主席点过名,他便觉得此人很了不起。正值青春好年华的艾克拜尔,觉得眼前这个活生生的人是作家,才感到“作家”也是一个普通的人。所以,他自己也就萌生了想当作家梦想。
在“文革”那个年代,图书馆被砸了,同学们手上拿到了不少书,大家也就互相传着看。就在那个时期,艾克拜尔至少看了不下一百部的长篇。
1973年恢复高考,他参加了高考,有幸被兰州大学中文系录取。按照父亲的意思,想让他继承家业,当一名医生,并劝说“搞写作容易犯错误”。自从艾克拜尔经历了许多事之后,也明白很多道理。他说,“医学院也不一定是为我开的,我选择它,它也不一定选择我。若是今年机会错失,那么来年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呢?很难说。再说上中文系搞写作的人,不一定都犯错误。”最终他说服了父亲。
文学之路从‘中央文学讲习所’开始
毕业后,艾克拜尔到了伊梨哈萨克自治州党委宣传部工作。期间,下乡、调研、参加“普及大寨县工作团”的工作,几乎走了二十多个县,一路走下来,不仅视野开阔了,也有了生活。由于粉碎“四人帮”,各种作品开始重新出版。艾克拜尔也开始买书阅读,1978年,他创作了处女作短篇小说《努尔曼老汉和猎狗巴力斯》,刊发于《新疆文艺》杂志1979年第三期,且荣获了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。
1980年3月初,他得到赴北京领奖的通知,途经乌鲁木齐时他去《新疆文艺》编辑部拜访,在这里获知他已被第五期“中央文学讲习所”(鲁迅文学院前身)录取。“确切的说,我当时觉得一片茫然。我不知道‘文学讲习所’是干什么的,更不知道它的历史。”他显得很疑惑。他说:“我不知道我被录取,还没跟单位请假呢。”编辑部领导说,“你是新疆唯一一个被录取的人,机会难得,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,也是我们新疆文艺界的光荣,我们会请有关部门向你单位打招乎的,你放心去吧,要珍惜这个机会。”
“文革”后第一期,也就是中央文学讲习所第五期,艾克拜尔与蒋子龙、王安忆、张抗抗等,共同来到了这里,开始了他们四个月的学习与交流。期间,讲习所聘请的导师之中,只因先前与王蒙先生认识,打心眼里认可他,而且对新疆生活王蒙先生很熟悉,交流起来很方便,故选了王蒙先生为导师,也算是缘分。
讲习所学习结束之后,中国作协有关领导就想把他留在北京,说是要创办《民族文学》,但是,他一心只想回到新疆伊犁州搞他的创作。最初,他是想走柳青式的道路,深入到基层,哪怕写好一个乡、一个村,但他发现,现实并非如此。
艾克拜尔发现,纵观文学史,很多国家的作家成名后,都会到该国的首都——政治、文化中心去。比如,英国作家到伦敦,法国作家到巴黎,俄罗斯的作家,也到莫斯科。1981年,艾克拜尔来到了北京,担任《民族文学》的编辑,一直就留在了中国作协。接下来,1985年中国作协创联部设立民旅文学处,艾克拜尔任首任副处长、处长一职,一干就是十年;后来在《民族文学》担任了八年的副主编、常务副主编,接着又到了中国作家出版集团担任党委副书记、管委会副主任,与大家携手组织起了相关机构工作,其间,兼任过《作家文摘·典藏》主编,2008年又兼任《中国作家》主编。
艾克拜尔是一个比较正统、严肃的作家,他从不瞎写,也不滥写,对于学术研究,更是严谨。从1989年到2009年二十年间,艾克拜尔中断了小说创作,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致力于历史研究和文学翻译,著述颇丰,撰有《穆罕默德》、《木华黎》、《关于〈蒙古秘史〉的成书、传播、以及哈萨克译文版对照》、《关于木华黎归附铁木真年代考》、《匈奴历史人物传记及族群迁徙流变考》、《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翻译问题》等。译有《阿拜箴言录》、《论维吾尔木卡姆》等译著。
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所引用的阿拜名言,“世界有如海洋,时代有如劲风,前浪如兄长,后浪是兄弟,风拥后浪推前浪,亘古及今皆如此。”正是出自艾克拜尔译著《阿拜箴言录》。另外,在阿克塞哈萨克自治县县庆50周年之际,由艾克拜尔作词,与著名作曲家徐沛东先生谱曲,合作了一首县歌《阿克塞》。
迄今为止,艾克拜尔出版包括小说、传记、学术研究、纪实文学、译著,已达二十八本之多。
他说,“这些年来,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,许多事需要重新认识,若匆匆忙忙的写,我也不愿意。我当了多年主编,一年要出一千五百八十万字的作品,为此还要阅读几千万字的作品。”
然而,自从艾克拜尔当了《中国作家》主编之后,他说,“我发现,大量的作品……”
此时,我随着他的话,扯了回来,反问,“是要去读吗?”
艾克拜尔迟疑了一下,说,“大量的作品……”
我又问,“是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吗?”
这一问,艾克拜尔笑了起来,他的回答,令我也觉得十分有意思。说,“我干吗要荒废呢?”
他说,“小说嘛,像水银一样,是游离的,富有张力的,若像钢珠一样能拿到手,就不叫小说了。”从此,他又拿起了笔,开始了小说创作。
他的小说,涉及少数民族、大都市、小人物等。他认为,“最新的东西不一定最好,速生的东西也容易速朽。经过时间考验,存留下来的东西才是好的。比方速食,给大家带来的是营养缺乏。还有,网络文学和有些畅销书,速生速灭。现在,每年出版三千多部长篇小说,一个读者哪能读得过来啊?”有的作品质量不一定很高。所以,他借用了高尔基的一句话,“制造语言的垃圾。”
对于语言的垃圾,他还用了个比喻,好如某些物件的豪华包装,拆开一看,里面的东西就那一点。那么包装呢,自然是被扔掉的“垃圾”。
自从艾克拜尔接手《中国作家》,便提出了一个理念,“用最优美的中文,写最美好的中国人形象,为全世界热爱中文的读者服务。”艾克拜尔有着自己的价值尺度,他尊重每个作者,对于刊发的作品,首先要充满正能量,积极向上。尽管当主编,但从没有过排他性,也不是说喜欢谁就发谁的作品。2010年,他把半月刊《中国作家》改成了旬刊,为《中国作家·文学》、《中国作家·纪实》、《中国作家·影视》。
2012年开始,《中国作家》开始转企,进行企业化经营和运作,自负盈亏。《中国作家》打造出了真正的文学期刊品牌。令人疑虑的是,纯文学也需要经营吗?
艾克拜尔说,文学是这样的:当作家写作时,它是个人艺术创作;一旦发表后,它就是社会的财富。作为期刊、图书一旦进入市场流通领域,它就是商品。所以,文学有其商品属性。任何一本文学书籍和刊物,都有几重价值。当你阅读时,它是精神食粮;从书店用人民币购回时,它就是商品;送给别人时,它就是礼品。
据了解,2014年月10月21日,《人民日报》刊发了关于《时代精神 创新意识——也谈“〈中国作家〉现象”》一文,并指出《中国作家》于国际国内打造了中国作家的形象。同时,也是文坛和党报对艾克拜尔所做贡献的认可和称赞。并认为,《中国作家》不仅以引领中国的纯文学潮流,也引领了中国影视文学的潮流。
当然,艾克拜尔时刻关注着现实生活,期间,他跟几个城市合作,推出一批文学奖项,比如“《中国作家》鄂尔多斯文学奖”、“《中国作家》剑门关文学奖”、“《中国作家》郭沫若诗歌奖”,“《中国作家》‘中山杯’华侨华人文学奖”、“《中国作家》‘舟山群岛新区杯’短篇小说奖”等。在这些获奖项作品中,有一批作品有幸获得茅盾文学奖、鲁迅文学奖、全国“五个一工程奖”。
艾克拜尔一直勤于写作,认为作家的黄金期是很短的,有的在青年、有的在中年、有的则在老年阶段。那么,对于艾克拜尔而言,他的创作高峰或许才刚刚开始。
自从他卸任《中国作家》主编之后,觉得自己轻松了许多,不再承担几十位员工的工资、以及退休人员的工资的压力。对于他自己呢,也就有了更多的创作空间。他说,创作是安静的,快乐的,是精神享受,而非孤独。哪怕于他坐在飞机上,也是要打开电脑写点东西。
“文学永远是人学”
近几年,关于60后、70后、80后的说法,越来越受到文学界评论家们的关注。当然,作家的同质化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,对于代际关系的现象,许多时候会令人迷茫。
艾克拜尔认为,那只是年代划分的方法,并非写作划分的方法。有时,甚至是一些慵懒的评论家省力的表述方法而已。文学若按这种规律划分,岂不是太简单了?当然,文学应该按流派、按风格区别划分。
在他看来,现在一说到按年龄段划分,就拿50后来说,噢,意识里会认为这些人老去了。这一代人,曾上过山,下过乡,插过队,甚至当过红卫兵、写过大字报,属于奋斗型,吃苦耐劳型。而60后,眼下正是挑大梁的一代。那么70后,开始是奋起的一代,自家里上有老、下有小之后,也开始变得沉默了。80后呢,大多都是独生子女。应该说,真正任性的是90后。然而,00后也在成长。如果从社会学角度去看,能讲得过去,若从文学的角度去说,似乎讲不过去。
是作品中关注的角度不一样?他表示,应该是这样。其创作经历、创作风格方面,也各不相同。关于“鲁、郭、茅,巴、老、曹”的现象,我读鲁院时,也是提得最多的。或许,每个时期的文学作品,都有它所存在的价值。
再比如,想了解人民公社是怎样的,要读浩然的《艳阳天》。 虽然人民公社撤销了,但那毕竟是中国的一段历史。1958年,三面红旗之一就是人民公社,若说了不利于人民公社的话,那就会打成为右派或现行反革命。1982年,国家取消了“人民公社”,改为“乡”。几十年过去了,人民公社到底是什么呢?想要搞明白,就要读当时的文学作品。这时,文学作品就起了一定的作有,自身也有了文化学价值、社会学价值、历史学价值。
谈到知青文学,艾克拜尔认为,知青文学有它本身的价值所在,但是有一点,某些时候,它只知道去诉苦、诉冤。从某种意义上讲,那些农民依然面朝黄土背朝天生活在农村,知青文学在倾诉时,似乎忽略了同样作为人的这些农民大众的存在。
他说,关于寻根文学,实际上是美国黑人在寻找他们的《根》。我们的寻根文学是把根寻到农村。比如现在城里的北京人,三代之前,多数人的祖上差不多都是农民。而今,2亿农民工的根在哪儿呢?还不是在原地?我国跨入新世纪之后,那些西方的文艺理论和中国的现实之间,毕竟是有些差距的,不能照搬。
目前,关于网络文学的大肆兴起,捧红了一些人。比如脑瘫诗人余秀华。我们先撇开余秀华诗的内容不说,其标题《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》,明显具有爆炸性。然而,她的诗句的确很有个性和张力,有些诗写得确实很好。他说。
艾克拜尔认为,现在是眼球经济、注意力经济时代,那些文商们,那些传媒、网络、经纪人,花样翻新想吸引消费者的眼球以获得利润最大化。它表明艺术的多重身份。艺术就是一个多棱镜。作品写出来,要放到社会上去,当读者心一热,就买下了,经销商们需要的是这个。比如手机网络,你这边点的是拇指,那边硬币就流到经营者的腰包了。
我们要巩固高原,再造高峰。所以,传统文化是决不能颠覆的,要继承,要发扬。正如艾克拜尔说,“文学永远是人学,写活生生的人,写人的情感,写人的精神状态,写人的内心,写出正能量。若把今天的‘人’写好了,就是对这个时代的贡献。”(作者简介:郭香玉,山东菏泽人。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二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。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、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。当代著名红学家林冠夫之关门弟子。)